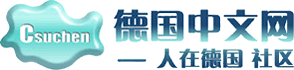|
  
- 积分
- 107660
- 威望
- 41024
- 金钱
- 6
- 阅读权限
- 130
- 性别
- 男
- 在线时间
- 3126 小时
|

[国际新闻] Made in China, read worldwide 中国文学在海外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novelists is creating a publishing sensation abroad
' v' V* U7 p- b2 k d8 S, D7 ]6 K8 W
21/07/20075.35.249.64& l' J& [3 T6 \" J2 d: d4 `) l6 x

0 z z! v, u! R; @8 [1 N g# g人在德国 社区
7 ^5 u \, u4 A2 w9 r5.35.249.64
) \4 R+ T# F7 }; x( c8 D. m当今世界最为畅销的女性杂志时尚( Cosmopolitan)杂志的主编海伦·布朗(Helen Brown)说,新的一代中国小说家正在海外创造一个出版奇观。' h. d; W R5 Y3 m' @4 i J
( d& _. C0 `5 S6 n3 q+ d5 v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导说,15年前,一本绿色封面的书从一个以小红本闻名的国家中脱颖而出。的家族传记记录了作者的外婆、母亲和自己一家三代女人在中国社会的人生经历:军阀的小妾,被背叛的革命者和最终成为一名作家的红卫兵。5.35.249.648 x, y: Y U+ ?' V. Z
# H! x" E9 Q1 g- S+ i% {% O如今,《鸿》的销售量已超过1,000万本,而且,长年累月是英国图书馆“出借数次最多的历史传记。”它不仅仅是个出版奇观,而且,对一名16岁时因为担心自己写的第一篇诗会连累到受迫害的父亲而把作品销毁的作者来说,这也是她的一次胜利。& P4 S, L+ c$ _+ I, A
5.35.249.64+ n3 p' M/ a! m0 M3 v
 # H/ _5 r* V% |9 Z) y # H/ _5 r* V% |9 Z) y
Western writers have either blunted or romanticised Chinese
6 }0 C& p, e, F
9 B4 g+ u1 T# b2 l g. Z; A4 `/ J自那以后,西方对中国书籍的胃口就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增大。通过像《鸿》和马建赢得的2002年库克旅行文学奖(Thomas Cook Travel Book Award)的《红尘》这类传记,我们步入了中国小说的世界。. M% ?7 W d G/ ?( w
* P: A3 I% }3 f* _% ]9 a
2000年,高行健以小说《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卫慧所著的煽情小说《上海宝贝》在被中国政府烧掉4万多本后,却在19个国家畅销。2 |8 q1 M" o- X0 e8 a
- j3 }; V% c6 d( Z1 n3 b
去年,郭小橹的《简明中英情人字典》入选英国专为女性作家设置的文学奖项柑橘文学奖(Orange Prize for Fiction)的复选名单。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被看好将会成为今年夏季末期的畅销书。1 R: s; x4 U' ?9 ?4 q$ A. @; r5 s
! Z: F9 J# \6 [$ `' P《为人民服务》的故事发生在毛泽东时期,故事中,一名身份低微的佣人和一名性无能的军区司令官的妻子玩起了危险的情欲游戏,打破那个年代的毛泽东神话。
0 ^- _2 m$ J) r- I" B人在德国 社区
% @6 v7 R1 S8 L) j, y' @, o8 L阎连科的小说倍受关注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小说的英文版封面上的“中国禁书”几个大字。
; ]* U; r0 I" {& K" o) U2 d0 }1 N: h
+ z3 M# E# ?. m/ X$ s# N8 i, a* f禁书往往是最好的宣传手段,被非西方政府禁止销售的书籍给予西方社会的人们两项快感:既可以享受到文学禁果,又可以在相互比较下,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获得一种自毫感。
1 K7 H' C; v& @# d( ?0 Z2 D0 Y, n
% _4 i% t: P* S1 ?/ A* W5 _' P/ u伦敦大学中文教授贺麦晓(Michel Hockx)说,一些中国作家专门希望被禁,好获得通往海外出版商的捷径。一些作者甚至假称自己的书被禁,但事实上,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理睬他们。人在德国 社区/ J5 t# `: i' L% P- T
w+ P, ^( b' U! }& q他说:“我认为阎连科的书是真正被禁的。”“任何公开攻击毛泽东形象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与西方诽谤法不同的是,中国诽谤法规包括已经过世的人。”“但是,如今在中国,只要你不攻击政府,就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东西。”贺麦晓教授还谈到中国本土上非常活跃的禁书黑市。
0 k: b$ k: [8 U0 L# s1 L* F! z' y0 L: X3 f8 B; l
文化经纪人托比·伊戴(Toby Eady)花了7年时间把张戎的书带进这里的书店。伊戴现在是麦克米伦公司旗下的斗牛士出版社(Picador)的亚洲小说顾问,他说:4 q# E( S) e* W2 H, _( }9 w
) L5 x% a' v3 o1 K; U( V
“现在,中国很少有禁书了。以前,他们曾经分为黄书和蓝书:黄书指色情书刊,蓝书指政治书籍。以前,我们会向当地的警察了解哪些书被禁了。但是,现在不同了。色情书刊不像以前那样被禁了。但是对政治书籍还是没有太大变化。”
1 m+ ?( R: ~# T$ v! _+ l人在德国 社区' b4 |- N V* s9 \5 S3 Y2 }
虽然,悲惨的传记在西方有不小的市场,但是,伊戴觉得他们对来自中国的作品并没有更大的胃口,尽管,《鸿》的成功曾一度使市面上充斥着这类作品。
* B1 D9 D: v* C! g0 r, U" L- w* H& w9 E& p* M' V: Y
他说:“我曾与梁卫(Wei Liang)和吴凡(Fan Wu)交谈过,他们两人都谈起他们在劳改营的童年生活。”1 M. x h% `! }, J2 o0 K; M
y6 v/ `: D' H/ {- N. i% O“两人的父母都是红卫兵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最成功的西方作者。这是中国人感兴趣的区域,因为,他们能将心比心。他们理解那种任何人都不允许高兴的日子。”( H8 p8 V6 `' ?0 ^- J! [2 O
3 b3 o6 W5 ?; D4 V/ B他继续说:“两年前,英国出版商首次造访北京书市。他们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就买下了不少书的版权。这是他们一种公共关系或者企业政治的一个方面。但是几年前,我被请去向几家大型出版商谈有关中国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必须要尊重中国的文化,出版翻译质量好的书籍,而不是盲音的翻译。明年出版的书会很多。”
8 X8 A3 v8 _7 x9 X L3 a* W- P! U! N- A" C( K: n7 G: E' i
伊戴认为语言问题是“一堵长城”,并表示那些用中文写的,然后翻译的小说(就如他妻子欣然的首本小说,《筷子小姐》)和那些由中国作者用英文写的小说(例如Liu Hong的《Wives of the East Wind》)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 x j$ J! y2 m# Q! Y) `# k
+ l* Z- c! d2 P# d Q3 p' P: ^他说:“我们欣赏博物馆和街道上的建筑、陶瓷、油画、翡翠和雕塑,但是,我们没法理解现实的中文会话。”1 y% c7 l- D6 J3 j5 l; j
. l! Y( H' v7 O" e! q" A+ T“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中文当成一种语言和一种思考方式呢?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读写,通过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理解中国,而不是通过西方眼光中的中国历史。高质量翻译要花很多时间,以及要有作者和翻译之间的合作。很少有出版商有那么多时间。”: L% c+ Q4 U1 Q9 e8 z
}4 Q0 ? w' _
20世纪的西方作家要么贬低,要么赞颂中国字,特别是文字的写法。现代主义者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称中国字为创造一种“时代艺术......对眼睛是一大享受”的“象形文字”:一种代表大自然的生动画面。中国有文艺评论家认为庞德具有“中国文化情结”,他的诗歌从诗学原则,诗歌语言来说都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
7 f0 H, ^$ l" m! i, D" g5.35.249.64
$ g/ N& T) a. v% E- m: t( ^薛欣然(Xinran)的英文翻译埃斯特·泰德斯力(Esther Tyldesley)把中译英的过程比喻成把云朵放入箱子内。其中,她特别着重点出,中国话中双关语几乎无法翻译的特点。尽管,她在中国农村居住了4年,丈夫也是中国人,但是,泰德斯力说,为了翻译《筷子小姐》,她与作者多次会面,了解许多有关南京的细节。/ q4 D9 I' q" z: F/ N
0 ] C$ e1 F/ B0 s- `9 `$ x |- [- p9 g她写道:“幸运的是,欣然一直都很乐意解答我的疑问。什么是阳春面?红卫兵拿那些妓院里的好纸张做什么?南京女孩肯定不会真的吃一个带着羽毛胚胎的煮鸡蛋吧?”6 o( f- o5 U. F+ o" i; R
( a3 `3 ~. t9 ?& W0 L
中英文之间,不仅在语言上,在叙事方法上也存在着文化差异。传统上,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地位要比诗歌低。1 e4 X% T# p, R" p7 h6 s1 O% R3 _! Q* q
. N1 L: s) Z* C/ c, ]) @散文式的叙事法出自口述的传统,而且,中文小说与西方小说相比,叙事手法没有那么直接了当。6 F4 P" J* ]' l
5.35.249.647 c, u) E: I" Z" g) N! F; k# a
另外,中文小说普遍有更多的角色:曹雪芹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有400多个人物。泰德斯力说:“有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在海外市场上。”4 e1 a% V6 k8 r4 {
3 g$ A+ F$ d& A; w, }5 C: V2 }3 r2 L今年夏季在英国出版的两本中国小说分别是努雷·维塔奇(Nury Vittachi)的《The Shanghai Union of Industrial Mystics》和中国旅美作家裘小龙(Qiu Xiaolong)“陈探长侦探推理小说系列”最新的一集《When Red Is Black》,两者似乎都属于西方叙事模式的写法。, o3 G8 Y. h/ \; a
' I# w/ x* q( c" o! `
两名作者都是用英文写作:维塔奇出生在斯里兰卡,现在是香港英文版书籍的畅销作家;裘小龙自80年代起就在圣路易斯居住。3 ^8 v, h# f9 O9 i' b W M5 V
: ?% r2 x# ^: U* Y' U人在德国 社区记者问泰德斯力,中国是否有惊险侦探推理小说的历史。人在德国 社区& _+ N8 z9 I# h
+ X8 f" _" ~! s j6 y
她说:“中国人也阅读侦探和推理小说,但是,主要都是从西方小说翻译过来的作品。在中国,这并不是一种受鼓励的艺术形式。原因之一,是这里的警察仍然对他们的工作保持着一种相对神秘的方式。在中国,你没有正式的警察程序。甚至现在,一种真实的做法大概还包括拷打嫌疑犯。”. r3 Z5 B6 |7 F' J: r8 C, @# {
5 j. N$ T, B. d维塔奇非常幽默。他用一名中国警探和一名马大哈式的澳大利亚助手之间的文化差异来展现出他的幽默。
6 P3 [# K. W8 W8 K- w8 H2 f5.35.249.64
+ ^/ C3 L- s) Z《The Shanghai Union of Industrial Mystics》的开端,是小说主角的办公室被毁坏:对风水大师来说是糟糕的一天。出生在上海的裘小龙则用他道德观复杂的侦探小说带领西方读者走遍上海。我们可以了解到那里的官僚作风、建筑和中国出版业。* c; C1 H6 A9 x# [% f
_7 x( L! y1 ~. I% A i% [1 Z
他说:“当我最初开始写作时,我的目的是写一本有关当代中国的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我的一些美国友人和同事仍然不怎么了解新中国,所以,我觉得向他们介绍一个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笔下不同的中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4 c2 V6 s% E- l" N; q
; B! K/ N+ S- s" k7 j& t* B还说:“我的书也翻译成中文,但是,因为检查官员提出反对意见说,‘上海不可能发生这种故事’,所以中文版中的上海被改为H市。翻译版也因为种种政治考虑经过了不少删改。”“一些人批评我,不满意我用英文而不是用中文写作。他们指责我崇洋媚外。”
/ S# d/ ]/ ]9 H. V5.35.249.643 l# D I7 ^. }* O8 `% c9 ^
就像伊戴一样,高行健相信中国作者需要用中文来写作,探索那种长期以来受文化传统压抑的独立性。
, o7 O7 c* [" ~! `- L8 G% k
) b3 t1 K- A1 a- z3 K. {! s在去年出版的《文学的理由》(The Case for Literature)一书中,这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道,“目前的中国语言适于探索精神活动和潜意识......但是,是否能够在尊重中文语言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发现一种更”流畅的交流模式,而不是充斥着西方语言的紧凑性呢?”电脑上表达简单讯息的文字,对文学并无助益。
4 u$ E/ R. u% `3 r$ U! y" p
* {2 _0 K3 ]3 S, K8 W, L7 a他认为,电脑上表达简单讯息的文字,对文学并无助益。“有了电脑后,玩文字游戏变得越来越简单;并不仅仅局限于单字和词组,甚至整句话都可以像麻将一样翻来覆去。”5.35.249.647 Q+ Q9 t) D, m6 @2 g [
5.35.249.647 [/ k; V7 Y* t! Z+ m
不过,高行健在91年说过,“汉语,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语种,就说这种语言的人数而言,有没有充分表述的自由?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从而造成作家心理上的自我约束,然后才是这语言自身的问题。一个作家写作原本只面对语言,却不得不先应忖这话多挤压,使劲去突破,这实在是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多余的负担,往往弄得狼狈不堪,以至于到面对语言的艺术的时候,已精疲力竭,不能不说是十分不幸。”/ o% s; t2 X: f: Z- e5 E1 z( t' z
) s" l9 m8 I+ Z# ^对中国文学来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是一个为西方译者与读者提供了美味的新挑战的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