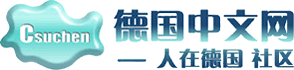|
  
- 积分
- 107660
- 威望
- 41024
- 金钱
- 6
- 阅读权限
- 130
- 性别
- 男
- 在线时间
- 3126 小时
|

2007年07月31日 新世纪周刊
; K a! V4 M# _/ c S6 c: ^* [6 `+ d+ H; h# _

- k o, ]2 g2 K' b% C1 G! i人在德国 社区+ [; m% g5 M5 z9 z7 ?2 X
-本刊记者/王巧玲
8 T8 l' U( ~2 e, I
( z( o& F- k4 ~5 @+ K 一本杂志要换主编,竟然引发知识界的大讨论,成为有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公共话题
" i7 O" y! N: V" r# y5.35.249.64( d8 V! Q% J. r; _+ V8 m
给《读书》的老作者陈四益打电话联系采访,“《读书》最近这么火!”电话那头的陈四益顺口说道。陈四益从19 89年起,就开始为《读书》写稿,为丁聪的漫画配文,应该算是丁聪之外,《读书》最稳固的作者了,经历了沈昌文和汪晖、黄平两个时代。陈四益说:“一本杂志主编的更替本该是一件自然的事情,现在却不知怎么闹得沸沸扬扬。”/ _. e" ]% N- t7 ~& i& h
# o8 M! H X% V% t0 A$ S
换帅,一波三折
( Y0 c0 m" } V" ]1 Y3 L) ]. Y5.35.249.640 P' Z' X' U% H
6月21日,北京某报刊登了“《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消息,拉开了《读书》换帅风波的序幕。此消息引发了人们的各种猜测,一时之间各方反应不一。加上《读书》杂志的一位编辑站出来质疑此消息的准确性,换不换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J& a b5 d" a. N0 ?/ w, ~/ l. n* q
# v& H. w: ~& e6 n9 E) a
在换帅消息传出的一个多月前,即5月份,《读书》推出了六卷的《〈读书〉精选1996—2005》。1996 年,学者汪晖入主《读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黄平共同担任杂志主编。《〈读书〉精选1996—2005》正是汪晖与黄平职掌《读书》十年的成绩单。在换帅风波依然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之时,汪晖、黄平带领编辑部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 《读书》10年文选座谈会”,王晓明、戴锦华等一些学界知识分子参加了座谈。在会上,近年来不绝如缕的《读书》“学术化”、“不好读”的老话题再次被提出。$ D7 Z9 i" B5 a4 K% X
5.35.249.642 O6 b/ A: z) m6 Z7 K
几日之后,《中华读书报》刊出《读书》确定更换主编的消息,换帅消息终于尘埃落定——汪晖与黄平将不再担任《读书》主编,改由三联副总经理潘振平担任主编,《读书》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但是风波并未平息,随后又有《读书》大多数编辑抵制人事变动的消息传出。风波在更大范围继续扩散,波及整个知识界,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
9 s+ q3 g2 q4 Q' U7 j. G2 }5 v* |: D% W# N+ _/ @$ t
时代之变,主义之争2 m4 U1 N$ \; H8 d! F
! W* O+ K. g G4 q8 v+ Y, b9 ~ 从1979年创刊起,《读书》历时近三十年。作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可小觑。在近三十年来,从来没有哪一本刊物,像《读书》那样,能让知识分子对它保持长期的关注,也没有哪一本刊物能在大批知识分子心中形成“情结”。# B5 a* h0 L3 [+ `. d
8 x& X( L1 n0 G5 W) L5 |. @ 有一句在80年代流传的口号可以证明当年《读书》在知识界的地位: “可以不读书,但是不能不读《读书》。”
6 i# O3 [& D" {/ N1 W! c* u
! r* F' W* r9 N4 c- ]! N* x3 B人在德国 社区 但最近十年,关于《读书》的争议日渐激烈。其大背景则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有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当“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黄平入主《读书》后,《读书》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主义之争”。
+ D- R+ m) l% f4 S* L9 x; M人在德国 社区
$ V3 s8 ~9 @3 L: ^, N3 h 在《读书》十五周年,即1994年时,学者刘小枫曾说:“从《读书》月刊十五年的历程中,可以辨识出诸多中国当代知识界的状况,当然,主要是知识界中思想文化者群体的状况。”这话显然在今天也依然适用。0 e3 b1 y4 [5 t6 g3 S W0 u2 L
1 I& T/ h8 r, M, q- C* R 由《读书》换帅风波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和激烈争论,即可见《读书》的分量,也可见《读书》所存在的争议之大。“ 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之中,观点纷纭、立场各异、各种争论纷至沓来,像80年代那样的、一种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汪晖和黄平在《〈读书〉精选1996-2005》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6 b! s3 |; E$ Y) j3 o5.35.249.64# i4 D+ h( u B/ v" c& w
即将30岁的《读书》将走向何方?老作者陈四益说:“《读书》不可能回到过去,只能向前看。”人在德国 社区/ V' k/ L5 Y/ q Z3 J
4 q: b7 l9 C; b: S! v( S
《读书》诞生记7 o: W) S3 d' A$ c2 S+ ]7 O
$ o4 K) s/ U* T5 [ 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在大时代背景下,立即引起知识界的关注,成为80年代的思想旗帜
/ o/ Y1 E5 Z' P& O
& y2 c. M8 t4 X6 W3 l# g* E' G人在德国 社区 “文革”期间,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被送往干校劳动,他们被称为“陈范集团”。在干校里,“陈范集团”开始酝酿一本读书刊物。2 n1 ?. ^& z7 }) h3 U2 B1 ?1 d
* B F6 O; u5 x. c1 G) D, k7 ~/ ]5.35.249.64 “大概在1970年前后,我跟陈翰伯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的事情,我们商定一旦有条件了,还是要办读书刊物,当时陈翰伯提议,杂志的名字就叫《读书》,简洁明快。”已83岁高龄的范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几乎无书可读,除了毛主席著作,其他的书都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这可把搞了半辈子出版工作、嗜书如命的三人难受坏了。 k; a+ N! E# J
/ d7 Y4 Y. @% `, k7 I 1978年12月,“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刚刚开过,陈原、陈翰伯、范用等人就开始实践湖北干校时期的设想,策划出版《读书》——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 N/ B4 Q+ H f( w6 B
5.35.249.64, t6 o" V$ z' ?+ h m% C4 F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创刊号就惹了麻烦。李洪林的一篇《读书无禁区》引起了震动。文章标题原本是《打破读书禁区》,但在发稿时范用把它改成了《读书无禁区》。“杂志出来后,主管出版的机关找我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不妥。有人说我们这不是在提倡看不好的书吗。我这人有一个癖好,好书、坏书都看,听说有什么不好的书,我就要找来看看。我相信,人们有自己的辨别能力。”范用回忆说。
; z$ B, f/ j8 G1 o3 y; E5.35.249.64$ I! W' K' q( k7 F/ @0 A+ s
创刊号的《读书》在《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套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范用找出一本厚厚的《读书》合订本,指出这些字句。“《读书》的宗旨、定位、风格都在这里面了。”这也成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读书》的编辑原则。5.35.249.64- u _% L( S3 X8 E' I/ U2 d
' b& S& }' a) [' T
“每个月,我们和编辑一起开一次讨论会,研究下期杂志的内容。我所负的最重要的责任是,阅读每期杂志的清样,然后签字,才能付印。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我退休。”1986年,范用和陈原离开《读书》,范用的老部下沈昌文接任了《读书》主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位。
! F) Q# _2 b% H3 _
+ y0 ?- M" j" a- N- T; d: o: D+ J6 h! n人在德国 社区 如今,陈翰伯和陈原已相继去世。83岁高龄的范用依然精神矍铄,范用家中的每间屋子都放满了书,其中有他编辑的《傅雷家书》、巴金《随想录》等,当然也少不了《读书》杂志,一套套《读书》合订本被高高摆放在书架上。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范用依然在关注着《读书》。人在德国 社区) F$ U3 K) Q1 r
5 o0 g+ g# n! c# `
“沈昌文时期的《读书》和之前的《读书》没有什么改变,基本上是延续。而汪晖时期的《读书》,我读起来,感觉不对头,文章越来越深,越来越长。不少文章我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南京开座谈会,很多人跟我提看不懂《读书》了。这个时期的《读书》拔高了,学术化了。”5.35.249.64 V# q# H" e, |- m, k* K# p& @
5 M, D* B6 A( u( b$ L- w
新上任的《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吴彬是吴祖光的侄女,曾在范用手下工作多年。范用对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和信心。 “吴彬从第一期开始,就已经在编《读书》了,一直工作到现在,非常有经验,完全可以胜任,我相信她能把《读书》办好。《读书》不是学术刊物,希望能回到以前的办刊思路,不要拔高了,要办给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看,给喜欢读书的人看。”
& h* e3 P2 Z: u5.35.249.646 J& ^2 A7 f# R5 H; C/ @
争议十一年' z/ k1 W/ s# t6 C
* R# |* r: t4 G1 w人在德国 社区 汪晖入主《读书》之后,它不可避免地被牵扯进那场旷日持久的学界之争人在德国 社区/ a$ X# r C4 } E
: H* p( u% R c2 J! @2 n- F* H
“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是汪晖和黄平为今年5月出版的《〈读书〉精选1996-2005》撰写的序言标题。而所谓“重构”,恰好是这十年引发《读书》争议的缘起。2 n, A j7 G% Y- c2 a
5.35.249.64# m E3 g. T8 N5 E4 u
1996年5月之前,《读书》一直是出版家办刊。之后,三联书店请来学者汪晖和黄平来主编《读书》,《读书》开始了学者办刊的时代。此后,《读书》已经坚持了十七年的“非学术性”和“可读性”传统风格,发生了改变。$ u1 K1 {7 W0 y: }9 Z5 L
z) F. z/ Y" d% F! b
有关汪晖、黄平主持《读书》十一年间的争论集中在两方面:《读书》是否已成为“新左派”的阵地;《读书》是否沦为学术刊物,文章是否学术化、晦涩难懂。
- i: y2 y7 J! I# ~4 ~3 t0 B- A, j- q" E5 G- C) Z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 之称都来自于西方学界。“新左派”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历史等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理论流派和思潮,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诸问题;而“自由主义”则是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5.35.249.64/ T0 A) O% ]0 d: _) e* s- i( p8 j1 L
3 q6 X* a; h) \7 Y- Z- L' a4 I5.35.249.64 但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国内“新左派”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甘阳等人,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李慎之、朱学勤、刘军宁、徐友渔等人。双方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病症开出不同的药方,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提出不同意见。新左派认为,中国已全面进入了自由主义主导的时代、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相勾结的时代,因此已应该着力提防市场的副作用以及外资的副作用。而自由主义派则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左派所指责的那样一个时代,中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建立起一个彻底的、完善的市场体制。他们指责新左派是把外国的问题当成了中国的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在这里大谈克服现代性的弊端。
. u$ h$ Y, G i+ k9 _( c
- I6 v2 [ }% h8 I. R7 Z人在德国 社区 当汪晖入主《读书》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刊物《读书》不可避免地被牵扯进这场旷日持久的学界之争;而汪晖的“新左派”身份无疑成为《读书》争议的焦点所在。
: m8 G( Y- U# O人在德国 社区" g# F/ _/ Z" }9 _
“让我惊讶的是有关《读书》的说法就两句话:一是说不好读,二是说‘新左派’。假定《读书》上的都是‘新左派 ’的文章的话,那么,中国知识界的图景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思想自由并不等同于每个刊物应该毫无自己的取向。中国这么多刊物,反对者为什么不去发展自己的空间,却要反复地攻击《读书》?这真是奇怪。??为什么《读书》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和攻击?我认为与它实质地触及了现实及其利害关系有关,也与它愿意向‘常识’提出挑战有关。”不久前,汪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5.35.249.64. b! ^6 R9 d9 g' [( X
, h6 g- d- @: N0 A1 u& q “在《读书》杂志中,真正读不懂的文章的比例是很少的。我们也希望更好读,但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理论性的和探讨社会问题的文章排除出去呢?因为那样只会造成新的单一性,这是很危险的。我很欢迎人们对《读书》提出的问题进行争论,对杂志进行批评,但十多年来总是说什么‘不好读’之类的话,这算是对思想讨论的批评吗?”显然,汪晖对外界针对《读书》的两方面指责,都无法认同。
1 n- d C4 f% V6 C/ ?
/ V9 p) i% g. A7 [ 在汪晖看来,为人诟病的《读书》风格之变是基于时代之变所做出的选择。“从90年代的市场扩张和社会分化,到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而剧烈的‘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知识界再也不能像80年代或90年代初期那样将市场化、私有化当作理所当然的尺度来衡量社会变迁,那些在80年代和 90年代初期流行的术语,如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等等范畴,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图景了。??正是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80年代,也不同于90年代初期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读书》以批判性的思考为取向,兼顾多重立场,自觉地介入90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引自《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人在德国 社区, H* A/ E7 q; T
% O/ z* Q: B% h: F4 ]' R% c) m
在这十一年中,《读书》探讨了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等问题。
; k6 Q; @ G$ Q( t8 ^1 L( I* A4 T0 }2 s: n9 N2 P8 ~ u' m
汪晖和黄平也曾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读书》进行了一番比较:“如果比较这一时期的《读书》和先前的《读书》,这份杂志的风格至少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杂志中有关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和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地增多了;第二,杂志仍以中国大陆的作者(以及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但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拉丁美洲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也成为《读书》的作者。”
: l" m& ^/ O# ~2 r3 b* g人在德国 社区+ J& F) _+ h; D- D! Y
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读书》这十一年来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和讨论,并没有切中时弊,甚至和中国现实发生了错位,一些理论在西方语境下更有意义。并且,“自由主义”还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何《读书》的主要作者都是“新左派” ,而之前广受读者喜爱的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的声音则在《读书》上消失?+ Q3 z% k8 _0 `$ p, F6 D
/ H! J# @4 D' ]* p, M% Q
沈昌文
! Y5 r$ f& L' v- X/ g' ?- a3 G4 D. P, _& O5 `2 x: m5 ^ c% g z
普及精英文化
6 ~' m/ r1 d+ u5 Z4 G
2 i$ H+ X$ |6 a7 c0 n( H 沈昌文,人称“沈公”,从事出版50年。沈公虽已76岁,却每天背个双肩包,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泡在咖啡馆,三更半夜在网上潜水,浏览名人博客。1980年,他到三联书店工作,开始参与编辑《读书》。1986年,成为《读书》主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直到1996年退休。" Q4 B. {) a3 L. Y7 D
9 k4 s3 E0 H W4 g 对于吵得沸沸扬扬的《读书》风波,沈昌文不置可否。“听说我还被卷进去了,我早退休了,现在的事儿我都不管。如果你觉得有意思的话,我们就聊聊以前的事。”/ P. x8 c; L! e( k: ?6 l& b
4 a/ I8 j1 ?/ o1 q/ @' \3 J& J 为什么《读书》在诞生之后能迅速成为一面旗帜,成为知识界的风向标?
) i7 N- u1 O( M5 Q人在德国 社区/ L) F! |9 K% P2 y5 g k& T
首先,《读书》出现的时机非常合适。《读书》在1978年底开始策划和筹备,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刚刚开过。当时的主编和策划陈原、策划陈翰伯他们把它定位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这对于寻求“思想解放”的氛围来说,非常及时和必要。从建国以后到文革,很多书籍都是禁止的。读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读书》的出现则显得意义非凡。这可谓是天时。5.35.249.64- S, `9 T" N+ a$ [0 c9 D8 D
1 o M+ ^2 S! [3 K 《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读书》的主编、策划和出版团队都是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出版家,陈原先生、陈翰伯先生、范用先生、史枚先生,他们早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办刊经历了,精于出版事业,他们为《读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应该是人和。
( s3 L% u9 W2 c z; o3 j0 \7 A! o, L: f
在知识界,有人认为《读书》形成了自己的文体,即“读书文体”,您怎么看《读书》的文章风格?; ?- p: a0 s" U- T3 E* D
. w- Y9 z8 H& _) q
《读书》的文体可以说是一种“厚积薄发”的风格。既具有思想性,但又不晦涩难懂,而是深入浅出,具有可读性。这需要作者具有很强的写作功力。比如金克木先生的文章,就是“厚积薄发”的典范。金先生是个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是他写的文章却是深入浅出,容易阅读。
0 M4 [: V6 T) v8 `人在德国 社区人在德国 社区2 }; o- B6 [* u
当年,您提出《读书》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可供他们“卧读”,特别强调文章的可读性,为什么?
M" m5 T! O0 s" w8 u& i" A- L; Z
+ R1 Q+ P" ~. d9 S0 c4 ~人在德国 社区 事实上,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在《读书》创办之时,陈原、陈翰伯他们就已经强调《读书》文章的“可读性”了,我不过是延续了这种风格。他们都是老一辈的出版家,对于出版业非常有经验,清楚可读性对于一本刊物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们早已确立了《读书》的定位,它不是一本学术刊物,而是思想评论刊物,而当时的一些老学者、老知识分子也特别认同文章的可读性。吕叔湘就曾经说过,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 reader(翻成 “一般读者 ”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读书》不发表学术论文,因为它面对的是大部分的一般知识分子。比如说“人的太阳必将升起”这样的标题,用的是一种诗意的语言,而《读书》不会用“论人道主义”这样学术化的语言。 @& M C( Q8 C
2 L9 ~2 ?+ l9 l8 y[ 本帖最后由 日月光 于 2007-8-3 09:30 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