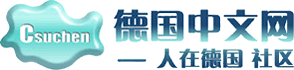|
  
- 积分
- 21920
- 威望
- 6300
- 金钱
- 1
- 阅读权限
- 100
- 在线时间
- 1355 小时
 
|
4#
 发表于 2006-8-24 12:07
发表于 2006-8-24 12:07
| 只看该作者

第一部分 第三节 将装蛋进行到底
我呆呆地坐在桌前,觉得大脑已经满得没有一丝缝隙。桌上那堆凌乱的邮件里
有封航空信,不用说是父亲写给我的。不过我现在懒得拆开。其实我对父亲的印象
实在说不上深刻。他一年只回来一两次,皮肤晒得黑黑的,明亮的眼睛里全是异乡
人的神情。小时候他总是把我高高地举起来,说:“让爸爸看看天杨又变漂亮了没
有。”吊灯就悬在我的头顶上,我在他漆黑的瞳仁里看见了有点胆怯的自己。父亲
在非洲一待就是十年。我十二岁那年,他因为多年来在非洲的出色工作得到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什么奖学金赴法国深造,几年后就留在那里,不过每年仍然会
把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耗在非洲。这之间他结过婚,又离了,我有一个从未谋面,
今年才五岁的小弟弟,不大会讲中文的混血宝宝就是这场婚姻的纪念。我把那封信
放到包里,站起来。把白衣扔进柜子。腿脚酸疼,真恨不得把鞋脱下来丢进垃圾筒。
走廊上的日光灯永远给我一种超现实的感觉。我喜欢这寂静。慢慢地走,踩着自己
的脚步声。从童年起,夜晚医院里安静的走廊就让我心生敬畏。不止走廊,医院里
的很多场所都让人觉得不像是人间。比方说爷爷的办公室,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
的地方之一。爷爷是放射科的主任,给人的身体内部拍照片。他站在一个硕大无比
的镜头后面,对病人说“不要动”或者“深呼吸”之类的话,只是从不说“笑一笑”。
他把X光片抖一抖,夹到灯板上。X光片抖动的声音很好听,脆脆的,很凛冽,可
是不狰狞。“这是心脏。”他指指一团白得发蓝的东西,戳戳我的小胸口。“是蓝
的?”我问。“是红的。”爷爷说。
我经常在下班的路上胡思乱想,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其妙处相当于学生
时代星期五的傍晚。感觉好日子刚刚开始,有大把的清闲可以挥霍。
我看见了周雷。那一瞬间就像梦一样。但的确是他。尽管我还不清楚他怎么会
突然出现在这儿。他站在走廊的尽头,有点羞涩地冲我一笑。还是和上次见面时一
样:笨笨的登山鞋,硕大的双肩包。
“嗨”我将信将疑,“怎么是你。”
“我刚下火车,”他答非所问,“就到你家去,可是没人,所以我来这等你。”
“我爷爷奶奶到厦门旅游去了。可是你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太突然,”他笑笑,“我被老板炒了。也巧,身上的钱刚好够买一张火车票。”
“那你爸妈”
“就是不想见我爸妈才直接来找你的。要是老头子知道我又丢了工作,不揍我
才怪。怎么样?收留你虎落平阳的老同学两天行吗?你知道刚才我敲不开你家门的
时候有多绝望呀……”
我终于有了真实感。“饿了吧?”我问他,“火车上的东西又贵,你肯定吃不
饱。”
“真了解我。”他作感动状。
我不仅知道他没吃饱,我还知道他不打电话的原因:躲不过是手机因为欠费被
停了。认识他二十年,这点默契总是有的。
走廊里空荡荡的梦幻感因着他的出现而荡然无存。我回到了现实中,腿依然酸
疼,但很高兴,三年没见这个家伙了。生活总算有一点点新意,暂时不用想明天还
要上班这回事。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这次从天而降,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变化,用“翻天覆地”
来形容,不算过分。
{周雷}
我站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地方,一眼就看见了你,天杨。
你慢吞吞地走着,看上去无精打采。你的头发是烫过离子烫的,我看得出来。
可是因为时间长了,新长出来的那一截不太听话,打着弯散在你的肩头。你绿色连
衣裙的下摆有一点皱,你的黑色呢大衣上第二个扣子不见了。可是这些都没有关系,
天杨,你还是那么漂亮。
我得从头想,我究竟是怎么站到这里来的。三天前的这个时候,我还和同事坐
在酒吧里很装蛋地点德国黑啤,听他们小声地用四川话划拳。我每个月的薪水就是
这么花光的。成都是个享乐的城市,本来很适合我。那我为什么把好好的差事弄丢
了?就是因为卫经理说我是饭桶吗?那个老女人对谁都这样,若是平时我还能说上
两句俏皮话把她逗笑,我相信她在骂我的同时也在等着我这么做。可是我没有表情
地把那个傻?“千媚”护肤露的文案摔到她桌子上。她吓了一跳,我也是。“老子
不干了。”我一字一字地告诉她。
一分钟后我就问自己:逞什么英雄呀,这个月房租都还没交呢。我平时不是个
冲动的人。那么是因为那张请柬吗?大红的喜帖,我当时都蒙了。打开才看见冯湘
兰的名字,她要结婚。操,她也嫁得出去,这世道。
她在请柬里夹了一张纸:“周雷,我希望你能来。”也真难为她,毕业以后我
去过北京、广州、大连、长沙、昆明,最后才来成都,她一定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
我的地址。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因为跟“清醒”摩擦了一夜而
升温。导致我第二天心烦意乱口干舌燥。我想这才是促使我丢了工作的直接原因。
天杨,我们高中毕业以后,我和很多女人睡过觉,大江南北的都有,冯湘兰是
其中之一。不,我想她应该算是我的女朋友,不过她从来不肯承认这个。
然后我开始回忆,在那个无眠之夜。这得从我的大学说起。
我是兰州大学毕业的。我的故乡的孩子都在为外面的世界努力着。就拿我和天
杨的母校来说,在那所全省最牛?的重点中学,没有几个人认为自己生下来是为了
在这个鬼城市过一辈子这城市潦倒也罢了,闭塞也罢了,最不可原谅的是连荒凉都
荒凉得不彻底满大街粗制滥造的繁华让人反胃。高考的时候大家一窝蜂地在志愿表
上把中国略有姿色的城市全体意淫了一遍。那些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上故乡的大学的,
肯定成绩不好。至于我,为什么是兰州呢,因为岑参高适们的边塞诗让我深深地心
动,因为我老早就想看看敦煌壁画,我还喜欢武侠小说总之一句话,一个人也许只
有在十八岁的时候才会用这种方式决定自己的人生。不仅如此,我还将装蛋进行到
底地在第一栏填上了“中文”系。我爸妈倒没说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能
考上第一批录取的学校。我走了狗屎运。可我一直都觉得,上天给我这个机会是为
了让我清醒清醒什么叫白日梦和现实的距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