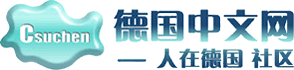|

- 积分
- 30
- 威望
- 12
- 金钱
- 0
- 阅读权限
- 30
- 在线时间
- 0 小时
|
5#
 发表于 2004-2-26 06:06
发表于 2004-2-26 06:06
| 只看该作者

獨白-阿紫
我悠閒的漫步在山間棧道邊,一面心不在焉地張望身旁的景緻。
哈,風景真是不錯,遠遠望去,寬寬闊闊,山稜分明,但全是一片綠,單調了點,可以的話真想將它染上點其他色彩。
掐指算算,偷溜出來已經十幾天了;我拿了師父練化功大法的寶器神木王鼎出走,那些個師兄弟也該追到這附近了。單身一人我不怕,那群呆子可沒我聰明哩。只是不知還要遊蕩多久,希望銀子還夠用。
走著走著,瞧見這山谷中有潭碧水,水上還搭著浮橋竹屋,好漂亮呀!循著小路通往谷底,上了浮橋,低頭一看,發現湖中成群悠游的魚兒。
"哇啊~有魚耶~"我一高興便捉起魚來了。不巧,眼一瞥,湖岸也有個傢伙在釣魚。
眉頭一皺,我喊著"喂,你怎和我搶魚啊!?"那人,像聽見了,也像沒聽見。
"說你哪!"敢和本姑娘搶!?我跑上前向他理論,順手便拿張網把他給罩了。
這一鬧,又一個穿白衣的不講理閒人來助陣,才頂他幾句,他一抓就把我扔下湖,害我喝了幾口水。
哼,算你狠,可惜我會閉氣。不過我偏要裝死,裝成具死屍再來對你下毒!
我半浮在水面觀察著,來了個高壯的漢子,還跟了個姑娘,看來大我一兩歲。他們說了一堆,就是不來理我,久到我快撐不住了,才有個少婦把我撈起來,帶進屋。她看來有些緊張,大概以為我真死了吧,她略微鬆開我的領口,接著摸出一樣東西───從我幼時便跟著我的一面金牌。
我沒睜眼,但她似乎很激動,除下那牌子便慌慌張張的走了,再回來時,聽腳步聲最少跟了三四人,她邊哭邊斷斷續續說著什麼金牌啊、女兒啊的。
有人扣住我的手腕把脈,我翻翻眼,刷的放了根毒針,耳邊傳來一聲驚呼。
房裡有四人,替我把脈的是適才才到的那漢子。
他身一偏,躲過了我的碧磷針,瞅著眉狠狠瞪著我;我也不客氣的回看他。
那少婦和扔我下水的男子對他道歉一陣,拉過我,直說我是他們失散多年的女兒。
呀,反了反了,我才看他不順眼著,救我起來就成了我爹!哪來的事!?但他們指證歷歷的告訴我,當年是如何送走我.留下相認的標記和金牌;看來是錯不了。
不過,他們是我父母又如何!?我從小無父無母,沒人管教沒人理,人人都說我是個刁蠻無禮又不受教的女孩,連師父和那堆師兄弟們有時都為我頭痛的半死,眼前我斯斯文文的雙親可難保受不受的了我,沒準兒哪天又說認錯人,兩句話就想攆我走。
突然外頭有人喊著四大惡人來了,房內所有人又一古腦的全奔出去,但見三男一女立在湖畔,來意不善。爹娘和他們辯了幾句,雙方大打出手,刀光劍影,殺氣森森。那個被我網住的釣魚人已經被放出來了,他和他幾位兄弟也去助陣,又以他本人打的最兇。
爭相殘殺,我可是見的多了,死個一、兩打人有啥希奇?
那個漁人很快敗下陣,身上被木棍戳了一堆洞,一口氣喘不上,死了。呵,這好玩,我想,下次誰敢惹我,我也在他身上戳個十幾二十個洞好了。
爹接上去鬥,可對手太強,眼看要稱不住時,那替我把脈的漢子出乎意料的救了爹,還逼退那四大惡人。
回到竹屋裡,爹娘向他道謝,那漢子自稱蕭峰,開口要求爹當晚到離湖不遠的清石橋相會,說時語氣客氣,但眼神晃動,似另有圖帧UZ畢,便帶著那姑娘走了。那姑娘從剛才臉色就怪怪的,不知怎了?正尋思,娘喊我,一應聲,也就忘了。
黃燈昏燭,人影搖曳。我窩在屋角,傾聽爹娘憂心的對話。今天來的那個叫甚麼蕭峰的,不知結了啥樑子,三更半夜要約爹出去。
正擔心著,白天見過,跟在蕭峰後面的姑娘來叩門,說約會取消了,他馬上要走,還交代要我爹好好照顧我和我娘。
她臨走前和我對望一眼,沒說什麼就離開了;而我,倒是越想越不對,那兇巴巴的蕭峰,何時變的如此好心又體貼?白天像要殺人似的,現在怎反過來關心仇家啦?
嗯,大有問題。
為了一探究竟,我悄悄跟在那姑娘身後也溜出去,看她變的甚把戲。她回到像是他們過夜的矮土屋,對著銅鏡三兩下就把自己扮的像爹一樣,又匆匆的走了。
果然,她是往約定的青石橋走去,而蕭峰當然早已等在那兒了。我不作聲地藏身橋下,窺視著他倆的一舉一動。
他問了些話,而她則用爹的身份全數承認了;他十分憤怒,一掌打在裝成爹的那女孩身上,帶著怨,帶著恨,帶著復仇時的殘酷與滿足。
天啊......那一定很痛...她整個人被震飛,鮮血和易容四處飄散,嚇的我捂住嘴。
蕭峰也發現不對,急忙跳下水接住她。水很冷,全身溼透的兩個人都在發抖,他幾乎要哭出來了。
天落著雨,雷電交加。他與她的對話雖有些模糊,但足以讓我了解一切。
被打中的,是我姊姊。她是為了他的尋仇計畫才犧牲的。
不知過了多久,他很小心很小心的抱起姊姊,走上橋,在雨中跑著,急著前往某地。
只是,還沒來的及走遠,懷中人癱軟的手,便脫力地垂下。他身子猛然震了震,停下腳步。
我和他都明白,姊姊走了。
他大理石般動也不動的僵立著,仰天長嘯。
大地一片肅靜,惟獨狂捲的暴風呼呼地吹,彷彿也在咆哮、在哭號......
不該再打擾了。
我噤聲,悄然離去。
也許,他會就這樣淋雨到天明,緊摟著愛人。
好難過。連我這局外人都感染了這不關己的傷悲。
從來從來,不曾見過誰,為了另一人如此肝腸寸斷、心魂俱碎。
是怎樣強烈的羈絆,才能將兩人緊緊相繫,至死都一意懸念?
這份情,比起親緣,有過之而無不及,比起過去我所見的所有,都要深刻,都要震懾。
懷著好奇、喟嘆,我心底更有一份欽羨。
有一天,我是不是也能明白?明白這份珍貴的情感。
有一天,我是不是也能得到?得到一份如他對姊姊般堅定不渝的感情?
我不知道......但我確信,如果他能待我那麼一點好,同對姊姊一樣,我一定也會付出一切,就像姊姊為他所做的,毫不猶疑。
隔天,他出乎意料的闖進我和娘的竹屋,對著爹寫的一幅字畫發狂,自殘到吐了一地鮮血,怵目驚心。
事情有些不對。有人在挑撥離間,他的仇人和我爹一點關係也沒有,而我姊,則死的冤枉。我和娘,跟另一對碰巧來找碴的母女,參與了姊姊入土儀式。
看著他一把.一把,不捨的逐漸用坏坏黃土掩蓋一切,心,也抽的緊。
結束,他又要啟程,讓那誤導他的傢伙給他個交代。當然,他也提到我,由於我姊臨終的託付。
我嘴硬,倨傲地用段尖刺的話回敬他。他沒再理我,風塵僕僕的上路,不顧瀟灑後一身清風中滿滿的愁緒。
當晚我隨人到馬夫人───爹的一個情婦家。他也在,馬夫人似乎就是害死姊姊的罪魁禍首。
隔著門櫺,聽她嬌聲嗲氣的對著個有婦之夫調笑,真教人不齒。
機會很快來了。趁她被點穴動彈不得時,我啊,就"輕輕"在她身上劃幾刀,削斷筋脈,然後淋些蜂蜜,等螞蟻來替她止痛。
我笑嘻嘻地靠在茶桌旁,冷眼瞧著她不斷掙扎著,咒罵著,她多罵一句,我就再多替她澆點糖水。
看著這樣一個愛美如命的騷貨,因為恐懼而五官糾結、全身紅腫容顏盡毀,還真讓人痛快呀!
居然和我娘搶我爹,又設計姊姊死在愛人手下,讓他們受盡折磨......
你該感謝我沒再用更狠的方式對付你了。
嘻嘻,別叫別叫,好好享受吧!看你來生還有沒有這膽,再有這附黑心腸!
曙色漸露,我跟著爹娘回家,可才到門口,就見到幾個人賭在那兒,一個個橫眉豎眼咬牙切齒,全是那跟我搶魚傢伙的兄弟。
冤家路窄,分外眼紅。我要爹作了他們省的眼煩,卻招來爹一頓斥責,說什麼養女不教、為父之過,反強著我向他們道歉、拽著我要去那死人靈前上香。
看吧看吧,才第二天,他們就嫌我、厭我!
我就是惡毒陰險,我就是刁鑽殘忍,阿紫即使有父有母,也注定沒人關心沒人疼!
悶了一肚子委屈,我趁他們沒注意就一聲不響,走了。
找到了家,卻又離了家,我正盤算著接下來該到兒去好,突然想瞧瞧被我斷筋螞蟻咬的馬夫人現在是怎個慘樣,就往她家走去;進了內房,卻見到他坐在床沿,正摟著馬夫人;那女的已經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還是照樣的愛勾引男人。
哼,這種爛人他居然也看的上,難道我昨晚眼花了嗎?
瞥了桌邊的手鏡一眼,我計上心頭,拾起它"好心"遞到馬夫人面前,看見自己醜惡的相貌,她居然就這樣被自己活活嚇死了。
他十分惱怒,事後我才知道,他只是要問出他的仇人。我壞了他的大事。
人死了,不能留下證據。我們一把火燒了馬家。
"我姓蕭,叫蕭峰。"看著淹沒在火海中的屋子,他面無表情。
"是,姊夫!"我歪頭瞥了他一眼,呵,他愣了好大一下。
"現在你可以回去了,去找你爹娘或師父吧!"
"可我就是從他們身邊逃出來的,怎能回去呢?"我眨眨眼,希望他會說要帶著我一道走。
"那你自己看著辦吧!"扔下這句話,他自顧自地走人。
"欸,你..."癟了癟嘴,雖然他沒同意,而且態度不佳,本姑娘還是決定跟著他。
追著追著,從市內飯館到郊外的樹林,他就是不肯停下來好好和我說句話,直到我裝著腳扭傷,他才肯停下來。正紮著腳,他卻忽然呆住了,瞧著我喊"阿朱",還一把抱住我,直到我開口他才愕然收手。
嘿,沒想到這不苟言笑的大呆子也會有這種窘態……心裡暗笑,決定整整他,於是嚷著腳痛要他背;他心不甘情不願的背我走一陣就又摔下我,自己去了。我不死心,繼續跟上,一會兒就遇到來追捕我的師兄們。他們對著我要神木王鼎,原本我想有他在就沒事,他卻扔下我,任我被師兄們綁去自生自滅。我在心裡暗罵著,以為這次就要完蛋;驚喜的是,晚上大師兄來審判我時,他還是出現了。在他的協助下,我逃過了制裁,還殺了大師兄,統領其他師弟。
他見了卻轉身就走,說我年紀小小就如此狠心,他不打算再理我了。他腳程快,一大步一大步的往前走,眼看我就快被拋在數丈外了,情急之下我對他大喊:"我姊姊就那麼好,你就那麼瞧不起我!?"
"你一輩子也比不上她!"他別過頭,冷冷的說。
一輩子......都比不上她...?
我回過神,騙人騙人,我才不信。即使是我姊姊,我也不相信她會比我好!
氣悶極了,我乾脆抱著身邊一棵樹大哭。
這一哭他倒是慌了點,開始要哄我,我邊哭邊喊讓我哭死在這裡算了。他開始只是笑笑,後來失了耐性便又走了。
為什麼...?為什麼他就是不肯看我?即使一眼也好啊!
好熟悉。他逐漸遠去的背影。
因為我從沒能和他比肩而行過。我一個被他視為惡毒的小丫頭,永遠只能在他背後追著他,找盡藉口黏著他。
但我不在乎,即使被視為死皮賴臉,只要他能注意到我,值得。
可是現在,怕是厭倦,怕是心死。
怕他再喚也不回。
不要走,不要走...如果你真執意離去,我也只能如此......
當他覺得訝異,我居然沒再纏著他而回頭找人時,我裝昏,乘他不備吐了根毒針。
───只要他中了我的毒針,全身痲痺,他就不能再離開我...不再離開────
針,他是躲過了,而且還下意識回了防身的一掌。
呵...真是自作自受啊......
眼前一黑,我什麼也看不到了。
好長一段時間,一切都是混亂的。像自高處跌落的白瓷,碎了滿地,無從聚合拾起。再恢復意識,手腳能活動自如時,我們身處在一個女真部落。
聽到仕女稟報,他似乎很高興,而且還會催著我吃藥,還會笑著問我身體好點沒?
是因為我沒死,他對的起姊姊,不用良心不安吧?有些心酸。
沒關係沒關係,我要的是現在。至少他仍舊為我擔心。
很快,我恢復了健康,不但偶爾能對他搗蛋鬥嘴,也可以騎著馬,和他一同奔馳在遼闊青翠的草原上。
一對大雁飛過天際,如影隨形,雙宿雙棲。
望著,各懷所思。
"姊夫,你又想我姊姊啊?"
"...想,每天都在想。"很簡單的一句話。短,卻沉重。
心裡明白,兩人都沉默。
一天,我和他又一道在樹林間賽馬時,遇見了隊使者,隨他們去見姊夫的結拜兄弟,遼國的君王。
正相談甚歡,探子便傳來遼國叛亂的消息。
生長在星宿海,我深深明白權勢遞移造成的鉅變與危機。即使身處局外,若對方真趕盡殺絕,連我們都會被拖下水。我勸著他,要他盡速離開,他依然堅持要協助平亂。我嘆了口氣,拗不過他,只得跟著。
敵兵雖多,但他一個人獨戰大軍,依然輕輕鬆鬆押了對方首領歸來。
因為此事,他被遼王封為南院大王,我則成了端福郡主。封的好聽,事實上卻悶的緊,大大小小的百官婢女,見了我們就一聲不出,跪在地上死都不肯起來。
幸好呢,過了一陣子,就有人來陪我玩了。
一天我和姊夫外出時,遇見堆被遼兵抓來的邊境居民。其中一個神秘兮兮的叫姊夫過去,拿了塊破鐵片就要殺他,被攔下還直叫著他是聚賢莊的游坦之,今天決心要報父仇,報不成便要尋死。
我在一邊聽的好笑,也窩火。這傢伙是什麼東西?憑他也要找我姊夫報仇?想的太美了點吧!?
後來姊夫放走了他,可我才不會讓他這樣容易走人。既然他要尋死嘛,我就成全他。嗯,反正我正無聊著,拿他來玩再適合不過,整人,我有的是辦法呵......
那傢伙呀,被我當風箏放,帶燒紅的鐵面具,獅子咬,順便替我練毒功;敢找我姐夫麻煩,就活該被我整。
當然,他不知道我在想什麼。他認定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叫他做甚麼都乖乖的,百依百順哩。
只是,看他因為被冰蠶咬而中毒僵死時,心裡,有那麼一點愧疚。
玩歸玩,他那麼聽話,把他弄死好像有點兒過意不去。深深嘆了口氣,最重要的是,現在又沒人陪我了。
王府的日子是孤單的。
縱然衣食無缺,日子悠閒,可當靜下心時,沉澱的.五味雜陳的過去總浮上眼前。
很久以前還在流浪時,我快樂,因為無牽無掛。
現在住在深宮院內時,我快樂,因為他在身邊。可總覺少了什麼啊.…..
待在他身邊越久,心裡越是空洞。深深的,無底的,難以探清。
不論何時,他目光總是穿過我,看向遙遠的某處,一個我不了到了的境地。
太遠,太難懂。
不論何時,他總懷著惆悵,單雁孤翔,漸行漸沉。
有次我從後面摟住他,趁他轉身之際在他臉上輕輕吻了一下,他僵在原地,臉上有著尷尬,然後推開我。
"我要是心情不好,就算吃一百個熊膽也不會好!"
"我姊姊要你照顧我,你卻這樣對我,反正我就是個沒人關心沒人疼的孤兒!"
我不管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他永遠是一號反應,走人,留下我......
為甚麼還要如此在意?空虛.忽視,全是我自找的,真是作賤自己。
終於有一天,我受不住了,偷偷溜出城,越過邊界回到中原。
路上我扮成個男人在館子裡午餐,好死不死遇到師父,恐嚇威脅不說,還被他和也在那裡小憩的慕容復開打時放出的毒藥噴上眼。
陣陣刺痛襲來,我放聲尖叫,因為我眨著眼望不見任何東西。正恐懼著,摸索著,突然有人一把抱住我,往肩上一扛就跑,打鬥聲和桌椅碎散聲被遠遠拋在後頭。
我不知道這捉我的人是誰,更不知道他捉我要去哪、有啥目的?
那人帶我遠離人群,走到一灣清流旁,讓我清洗眼睛。我視力幾乎全失,連物體的形影都見不清。
救我的那人說他叫莊聚賢,他會保護我,不會離開。他怎麼對我這樣好?我們素不相識吧?疑惑,但是有人願照看我總是好的,不然我現在這副慘樣能做甚麼?只會死的不明不白。
對,我還不能死,我還要回雲州,我還要回去見姊夫,和他一道打獵觀雁。
我央求莊聚賢帶我回雲州,現在,我只想他在身邊。他似乎為難,但答應了。但事實沒有想像的容易。我們不僅沒回到雲州,反而流落到了丐幫,莊聚賢還意外的當上幫主。我眼瞎不能自己行動,回不了雲州,只能定在這兒,當真鬱卒的不得了,那些個叫化子又愛在暗處指指點點我的眼睛如何如何,我一火大,便拿他們來很狠修理了一頓,他們嚇的個個敢怒不敢言。
一天,莊聚賢突然來告訴我要去攻打少林。我邊聽邊呵欠,他攻少林關我甚麼事?沒想到他還隱約提起,星宿海的星宿老怪虎視中原已久,可能也會去。
我一聽,馬上怒火上升。儘管丁春秋以前是我師父,但他不顧師徒之誼,我不過借他寶鼎玩玩,他便要殺我,還毒瞎了我的眼睛,此仇不報,難消心恨。
當日,我便備了一堆以前常見的旌旗帷幕,大搖大擺的到場,果然丁春秋和師兄們都在,我便要他給我下跪磕頭;反正莊聚賢武功也高,用不著怕。
誰知丁老怪老稚钏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