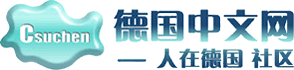|
  
- 积分
- 35112
- 威望
- 4858
- 金钱
- 20
- 阅读权限
- 110
- 性别
- 男
- 来自
- 中国
- 在线时间
- 4434 小时
|

中国必须摈弃前苏联的民族政策
(2009-07-11) 人在德国 社区% M ?* Z4 F; P$ I) @1 _, b
● 汪应果
5 b/ p; q0 V+ Z, T( b* [人在德国 社区
+ d* L5 x' B# M/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各族群的大融合,才造就了这个民族总体上基因较好、智商较高的优势。现在人为地分隔族群,简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 j( R2 t$ g# e! m
0 w! Z" u: i; v: Z$ D" n7 q" y) o; }汪应果(澳门)
' j. o7 C/ F& h* }( F J
' K$ w [% q- P! J9 Y1 C人在德国 社区7月5日,新疆地区发生维族殴打、杀戮、焚烧汉人的骚乱。维族人一直在广大汉人的心目中形象相当美好,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中长得最美丽的族群之一,这一来,形象大打折扣了。$ q" ~) p* n, k! H5 |4 e
; K, l7 L% P9 j- J& J 发生这样的事,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但归根到底,不能不反思我们长期执行的所谓“民族政策”是否从理论上就有错误。
+ Y* `" _5 O# F; l' Q人在德国 社区$ d% B) {% V0 B. T
一年多以前,当西藏拉萨发生骚乱时,我就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就指出了中国长期推行的民族政策的理论错误,但政治家显然不屑看我们小民的意见,于是一年后,相同的悲剧重演,只是地点换了新疆。/ Y: X5 n9 u6 [0 y
, N& |8 ~4 j/ B+ C
在那篇文章里,我从美国的经验里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长期从前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民族自治制度”是不正确的,原因是我们把“族群”或“族裔”(race)错当成了“民族”(Nation),于是自找麻烦,种下今日之苦果。
6 J% ~) r8 Z3 W# O人在德国 社区( Q x* f. a( {- k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把原先的文章再发一遍:
( e+ w' U4 w" Z5.35.249.640 L: o2 m9 F7 L) e E0 Y
必须加强大熔炉力度: U. u8 c6 H, Y" A7 Y
. ]; y! ^' X6 j; y" o2 Q2 E0 o
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英语是Nation)叫“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基本理论上犯了知识性错误,沿用前苏联的概念,结果造成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问题,埋下了借所谓“民族问题”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隐患,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1 u3 W' \1 e h' B! Y) |' X9 S o
) a: V( a' Z' H0 m0 ~* N! n5.35.249.64
9 h% L5 |& M, }* z9 t 现在的56个民族应称之为“种族”或“族裔”、“族群”(英语是Race),他们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一口锅里轮饭勺,理应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过多地强调“族群差别”是不对的。
% Z' ]- c! t. X ~7 V! ~ “民族”(nation)与“种族”(rac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英语里nation具有“民族”、“国家”两个解释,说明同一个国家就是同一个民族的意思。9 ]5 l1 k8 ~% h: y8 W! ?
$ M( v( |- Y' t9 u 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内,各族裔的历史趋势应该是:加速融合的过程,就像美国那样,是大熔炉。在美国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很深,但黑人不是“民族”,统称“黑人”;同样,中国人移民美国就不称“中华民族”了,统称“华人”、“华裔”。中国也应如此办理,统称“汉人”、“藏人”、“蒙人”等等,这里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有族群差别。这就跟平时说的“上海人”、“北京人”、“江苏人”、“客家人”等等是一样的。人在德国 社区. L7 L* ?! T' l' g8 ?. }) y* S' l4 l
7 [9 V9 I, ]3 [0 C: G& W 中国必须加强大熔炉的力度,坚决搞大同。
4 |5 o' R; j6 Q
; F9 ]: m) i+ X5.35.249.64 中国“民族委”是否该考虑换个名字?所谓“少数民族”政策是否有重新审视的必要?5.35.249.64; l5 l# ?( i1 ]% |9 ?' [. O% [
( p; N7 A) K0 {& p
表面上看是两个概念的混淆,实际上是认识出了问题,它造成的错误是:7 s% y- ~1 z2 A3 D. s$ W
& [2 t, X4 L* i3 c' P, I% Y
民族自治政府种下祸根
; o/ d' `: t" U9 O; _" Q* X9 ?; L# I- H4 n6 C
一、概念混淆的结果,是成立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自治政府”,这一来不是缩小族群的差异,而是扩大甚至是把差异从此凝固化、永久化。因为“Nation”又有“国家”的含义,于是就为所谓的“民族”分裂分子提供了“独立建国”的理论基础。
" Y k, g" ?* {" ~' Y! v
; ~* R1 H, ]3 j 二、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56个民族”,这又是一个不科学的提法,又是一个分隔族群反对族群融合的提法,我不知道“民族委”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民族”?以血统吗?那么请问“汉族”难道是一个血统吗?所谓“汉族”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它跟比较单纯血统的“维族”“哈族”等等不是一个概念,它们概念的内涵不在一个层次上。) Z/ j0 Y, F* x/ l# u' U7 Q
. R" E# v+ Z7 I/ a9 p; W3 j
笔者本人头发就是自来卷,笔者的母亲、孩子、旁系亲属的后代统统是自来卷,以致几家人的后代(包括重孙女)不久前几乎不约而同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妈妈,我们有外国人的血统吗?”“为什么别人都说我们像外国人?”但我们是“汉族”。
p+ P* x2 Q2 X6 W& \5 e( {5.35.249.64" i: x; O1 b5 N& g1 G J
我的回答是:“说不定我们的祖先有哪个小伙子唱着‘胡姬貌如花,当户笑春风,’看上了一个‘当垆胡姬’也未可知。没准我们的老祖宗就是一个维族姑娘。”今天的汉族可说是早已融合了几十个上百个不同的血统了。
r' N4 T6 H( Y" G5.35.249.64 再说,所谓“56个”,那么澳门葡萄牙人的后代、香港英国人的后代有的加入了中国籍,为什么不算进去?
& f; R( o7 P/ K4 R' s. }- D
/ g. ?5 _3 s! v/ k2 |4 j9 I 三、一个国家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族群融合是他的大趋势,这是顺历史潮流而动。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各族群的大融合,才造就了这个民族总体上基因较好、智商较高的优势。现在人为地分隔族群,简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 l* O7 E2 O1 J9 i4 D& u: Q3 @2 B/ I+ t, J0 Z6 Z, b
四、秦始皇纵有万般罪恶,但他的“书同文”,保证了中华民族不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百个公国,使欧洲人民饱受几个世纪的战争之苦。这里一码归一码,功过要分清。而今天的“民族自治政府”则种下了中国日久分裂成56个国家的祸根。5.35.249.64, ?! B" h8 d7 ~# D, r/ s! Q0 }
& ^7 i4 _+ n; ?调整“族裔政策”
3 B8 } C2 _# G2 E6 n0 B3 `$ j
( j& W4 t P k 鉴于以上几点,中国必须重新认识、重新调整“族裔政策”,我的建议是:
+ W7 j8 {' m: Q1 p$ s# q+ ^1 j: o6 q
. m8 b8 U3 u$ t 一、重新对全民族进行一次“民族”与“族裔”的知识教育,把理论搞清楚,统一思想。4 ~3 k: f6 H' _4 g
! P7 w c6 H( [ 二、撤销各级“民族自治政府”,各族群没有独立的政府权力,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公务员的队伍,参与政府管理,各族裔权利平等。这就像美国的赵小兰、骆家辉一样,他们没有华人的政府。这就为日后扫清了分裂的隐患。5.35.249.64; U, m1 G7 p- E& q. {3 {1 ?' ?6 u
4 X8 v5 Z# [. m
三、对少数族裔集聚的地区,进行经济上、开发项目上的倾斜,发展他们的经济,让他们渐渐跟上汉人的发展步伐,渐渐富起来,但取消其他比汉人高一等的待遇。少数族裔必须认同“归化”,就像美国、澳洲等发达国家一样,必须向主流族群归化认同,必须学中国话,否则不能享有中国公民待遇。
. T2 E* E ]; y( u/ O$ h, H* a. H
0 c3 `( P3 H9 b; [4 N 四、鼓励并支持少数族群保留自身文化传统,但同时推进各族群婚姻大融合,推进各族群进入人口较少的地区,搞大移民,大混合。9 a+ U/ y' t4 O: t) R
8 R) N& O) h# z8 S% B' M5.35.249.64 五、学习当年王胡子王震将军的做法,让少数族群中的某些人又敬又畏。人在德国 社区& u% I1 F4 C. Q4 W
对此次打砸抢坏头头坚决杀无赦,对罪行较轻的能不杀就不杀,但要进行终身管制,一律分散移民至汉族地区,进行消化瓦解。这方面可学美国警察的做法,对有轻微偷窃的人,警察每晚必上门天天教育。
D. s/ x2 \# g2 i- s# X* N% G f1 g* g; V
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中国的所谓“民族问题”可大定矣。
6 ?! b) C% U3 s: O+ z* K
6 Q% u5 Z! ?4 J$ p% q. S% l 作者是南京大学退休教授,现在澳门大学任教 |
|